shān條兒 jiě 論:

瞅瞅評論區——
你們看的,真是一部電影嗎?
有人罵“爹味”沖天,拍的不是郎朗,是超級大爸;有人喊“飛”得離譜,姜文夢到哪拍到哪。
姜文電影的評論區,永遠比電影本身熱鬧。
可Sir看到的,還是那個放肆的姜文:他壓根兒沒想伺候所有人,甚至只想取悅自己。
這正是你不用跟風捧他臭腳的理由。
不管你喜不喜歡,但有一點,姜文絕不會讓中國電影無聊。
而且無論正反都是“人間”的事。
可姜文的電影,向來在夢裏、在天上,至少在只高於俗世一層的“房頂上 ” 。



拍郎朗?
那段比鋼琴還沉的童年,那麼確鑿又家喻戶曉的故事,怎麼可能飛上房頂?
可姜文就不講道理地飛了。
電影開場,他就左腳踩右腳,嬉皮笑臉地離開了地面。

“喫了這些藥片!”他邊說,邊遞給我一個藥瓶——我後來才知道瓶裏裝的是藥性很強的抗生素。“現在就把裏面三十片藥片全都吞下。吞下去,你就會死,一切都會結束。”
......他尖叫道:“如果你不吞藥片,那就跳樓!現在就跳下去!跳下去死!”
......父親喊道:“你要是不跳樓,那就吞藥片!把每一片都吞下去!”
誰看誰窒息吧?
可惜姜文覺得所謂“壓迫 ” 是小事一樁,這裏面有更拿人的東西——
是荒誕。
是 父子關係的錯位 。
爹沒個爹樣,娃也是。
而誕生這種錯位的,是一種令人敬佩的甚至令人陶醉的執念與瘋狂。
於是,他把衝突搬上他愛的屋頂,悲劇扭頭變喜劇。
郎朗、郎國任不再是父子,而是一對靈魂伴侶。
是的。
世界上有一種父親,在他的精神層面上,與自己鑲嵌得最緊密的不是妻子,而是兒子。
(還不能是女兒。)
於是你看到了這種“我和我的兒子,一刻也不能分割”的關係。
“你都讓老師開除了!”
“他開除的是我嗎?開除的是你!”
在一片五彩斑斕如夢如幻的積水中,朗朗父親爲救兒子一記滑鏟,把兒子進一步踹到了天上。
這是一聲宣告:
接下來的一切,都將凌駕於生活之上。
接着“你行!你上!”的標題出現,瘋狂啓程。

姜文電影總繞不開一個主題:背離時代的人,在動盪時代中的命運抉擇。
《你行!你上!》的動盪時代,很明顯,是90年代。
一幫被解散的民樂團職工,擠在破舊澡堂裏,你一嘴我一舌,議論郎國任兒子的鋼琴天賦。突然,澡堂停電,黑暗中,瓷磚縫裏一塊硬物閃閃發光。
像金子,可沒人敢打包票。
但哪怕是塊石英,它也得狠狠發光——因爲這幫人太需要這道光了。

好在,他爸也是瘋子 。
《一步之遙》裏,馬走日都要考慮考慮“to be or not to be,這麼着還是那麼着?”;而《你行你上》父子倆成爲“天下第一”的信念,從幾乎從頭到尾都沒有被動搖過。
郎國任的背離時代之處就在於:
在那個怎麼着都行、路越換越寬的時代裏,他是個一條窄路走到底的狠人。
電影裏有一段取材自現實的經歷:郎國任年輕時考音樂學院,超25歲禁報,老師讓他填24歲。他卻在年齡欄加了個括號:“真實年齡25”。
有點直,有點憨。
但之所以敢將一切都押注在孩子的前程上,還需要一樣別人沒有的東西,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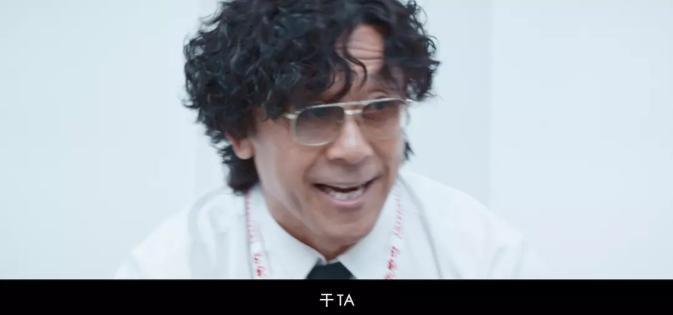
電影把它具象化了。
在舉家搬往北京的路上,最搶眼的,是一座有點怪異的,紅得 油光鋥亮的 主席像。




你只能裹挾在“一切爲了第一”的,狂飆突進的敘事洪流中,毫無停頓,只能任由姜文的狂想帶着你飛向更離奇的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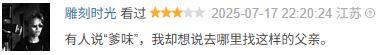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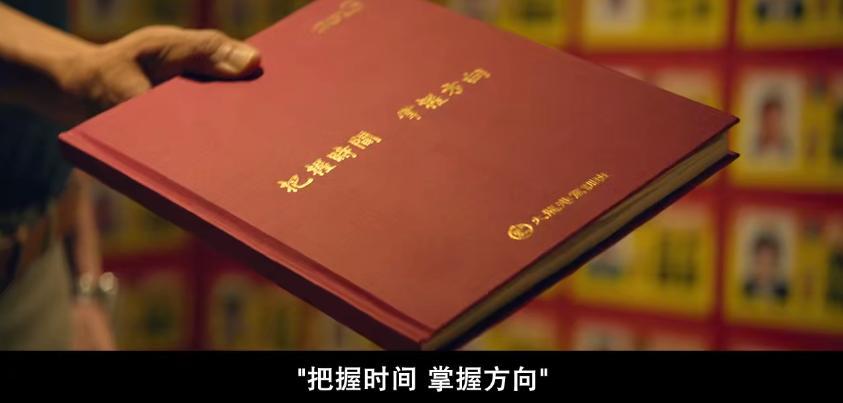


有讓你困惑的,有讓你着迷的。
總有讓你懷念的。
慣着他?行,但不必部部都捧上天。
批評他?也行,但別扣帽子搞倒搞臭。
這是爲了電影。
也不只是爲了電影。
“一般談到他,不管大家對他某部電影的看法如何,他的電影票房、獲獎或成績怎樣,有一個評價是普遍有共識的:中國需要有這樣一個人。 ”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