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夏夜,27歲的文浩做完最後一組俯臥撐,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拿起桌邊的藥片和水杯。作爲社區工作者,他白天穿梭於街巷爲居民排憂解難,夜晚則按時服藥、鍛鍊。
10年前那個驚慌失措的少年,腦子裏只有一個最樸素的想法,得病了就要快點治。正是這個決定,將他迅速拉回了生活的正軌,就像生活裏一瞬間掀起了驚濤駭浪,很快又得到平息。

2015年,國慶假期結束後,文浩坐在縣疾控中心的醫生面前,滿臉通紅,雙手不停揉搓,手裏的確診報告被他捏得佈滿褶皺。他聽到坐在對面的醫生說:“你還是叫上家長再來一次吧。”半晌,文浩嘴裏擠出哀求:“能別告訴我父母我得這病的原因嗎?求你……”
成長在貴州偏僻的農村,高二在讀的文浩心中塞滿青春期的慾望。生物書上寫着“不潔的性行爲會導致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傳播”,但老師對這一部分的闡述只是含糊帶過。
那會兒,文浩對使用安全套等措施沒有清楚的認知,也不明白保護自己的真正含義。他以爲生物書上的疾病離自己很遙遠,直到這個懵懂又衝動的少年與陌生人發生了幾次無套性行爲,病毒開始悄無聲息地侵蝕他的身體。

圖片由AI生成,形象不代表文中人物
不久後,17歲的少年開始持續低燒,後背長滿疹子,整個人提不起勁。他像往常一樣幫父母去山上幹農活,卻毫無力氣。文浩獨自去網吧,將自己現在的身體狀態輸入到網上,“艾滋”,“絕症”……這些跳出來的詞彙猙獰而刺眼,讓他愈發害怕。他在忐忑中,獨自去縣裏的醫院做了檢查。
在一系列的檢查後,醫生讓他再去一趟縣裏的疾控中心,在那裏文浩又採了一次血樣。過後幾天,文浩一直惴惴不安,他不知道等待他的結果是什麼,是生命的審判還是虛驚一場。
當拿到HIV陽性的確診結果時,文浩只覺得“天塌了”。翻湧的悔意和源源不斷的問題環繞心頭:爲什麼是我?我快要死了嗎?我要不要告訴家裏人?我能夠被治好嗎?……
疾控中心的醫生表示,根據規定,一定得告知他的父母,不過願意幫着他和父母溝通,同時也告訴文浩,越早治療越好。
於是在確診後的第4天,趁着要開家長會,文浩編了一個“在學校和人打鬧玩時受傷感染”的理由,帶着不明所以的父母再次來到疾控中心。
父母在診室和醫生交流時,文浩在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如坐鍼氈,短短十幾分鍾,時間被無限拉長。他不知道如何讓只有小學文化的傳統父母接受自己的孩子感染了HIV的事實。

圖片由AI生成,形象不代表文中人物
終於,父母走出醫生辦公室,只告訴他,醫生說這裏開不了藥,要把治療檔案轉到縣中心醫院,並報到拿藥。文浩設想的責備、謾罵都沒發生,好一會兒,母親才說,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一旁的父親也沒有過多言語,只是立刻和一家人趕往縣中心醫院。
怕看病來不及,父母一路小跑,“快點快點,萬一人家下班了查不了怎麼辦?”
在中心醫院,父母陪着他抽血體檢,取報告,再去感染科報道。從確診到開始服藥治療,文浩只用了4天的時間。他牢牢記着醫生的囑咐,先把藥喫上,一切都還來得及。

剛開始治療時,服藥隱私性成了巨大的困擾。文浩從來沒有在一天裏喫過那麼多藥,而且每天都要早晚各喫一次。爲避免同學疑心,早上他一定要在出門前喫完一份藥,晚上他就在晚自習前,以最快速度跑去廁所,把藥塞進嘴裏,再回教室喝水吞服。
還沒適應藥物時,他常頭暈犯惡心,記憶力下降,升入高三後,課業負擔重,他更加緊張,擔心自己容易漏服。過了數月,文浩才慢慢適應。
治療的同時,文浩也在不斷調整心態。文浩從小長得秀氣,他有一張照片留着長髮,白白淨淨地像個女孩,大人便總拿這個打趣,也喜歡給他穿女孩的衣服,拿他當女兒養。
文靜的他與山區周遭粗獷的男生不同,他也因此遭遇校園霸凌——男同學在上廁所時扒他褲子,女同學則嘲笑他像個女生。文浩嘗試過反擊,後來漸漸麻木。
感染HIV讓內向的文浩一度更加自卑,在學校受欺負也不願意和家人說。文浩有個弟弟,外向,壯實,走在路上輕鬆和別人攀談,也更加討父母喜歡。
文浩假裝過外向,但裝了一兩天就裝不下去,“讓我見人就打招呼,我講不出來……”青春期的迷茫加上患病的壓抑折磨着他,最絕望時,他想過“不想喫藥了,一了百了。”
文浩就這樣一邊克服情緒上的波動,一邊按時服藥,小小年紀的他並行不悖地應對着心理和生理上雙重壓力,好在都堅持了下來。除了藥物時不時帶來的副作用之外,HIV似乎並沒有給文浩的身體帶來其他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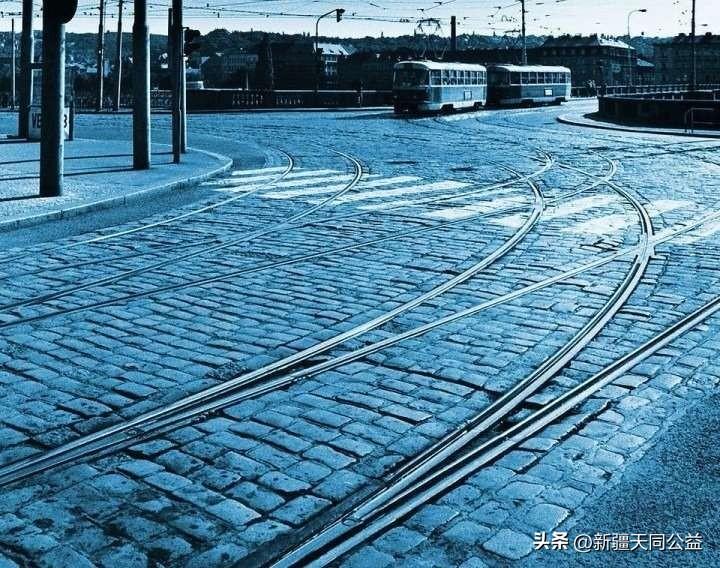
2016年,文浩考上了貴州一所大學,讀了社會工作專業,開啓了4年的大學生涯。2021年,大學畢業後的文浩來到四川自貢謀生。對他而言,痛苦的時光終於捱了過去,新的環境裏,一切都在向好轉變,病毒似乎連同那灼熱的青春期一起遠去了。

後來,文浩在成都找了份專業對口的社區服務工作。如今,他仍堅持每三個月複查一次身體指標,生活狀態與常人無異。
在社區工作時,文浩需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曾經內向的他,在工作中努力展現出積極熱情的一面。爲了保持健康,他堅持睡前鍛鍊,或選擇騎自行車通勤,生活看起來平靜規律。
然而,在文浩的內心深處,他依然覺得與家人,尤其與父親之間似乎還橫亙着一道無形的牆。他總覺得活潑外向的弟弟更受寵愛,自己則像個邊緣人。獨自在外漂泊多年,他也很少主動聯繫家裏,與父親的交流更是寥寥無幾。
打破這層隔閡的,是一場疫情中的斷藥危機。2021年,文浩老家的村子趕上封控,而他的抗病毒藥只剩下約一週的量,而拿藥必須本人親自到場。
HIV的治療不能斷藥,文浩焦慮得不知所措,他控制不住去想最差的結果。萬幸,村子幾天後解封,幾乎是第一時間,一向沉默的父親騎上電動車,載着文浩去拿藥。坐在顛簸的後車座上,文浩終於意識到,父母不是不愛他,只是不懂得如何表達愛。老兩口總是以另一種方式關心着兒子,對他的愛並不比弟弟少。
工作穩定後,有一年春節,文浩買了幾個按摩儀,分別送給父母和親戚們。母親很珍惜地收在閣樓上,嘴上卻表現得平淡:“一天天這麼忙,哪有時間用。”平日裏,母親是主動給他打電話的那個,詢問他是否堅持服藥,缺不缺錢,工作如何了。每到文浩要去醫院拿藥的日子,母親比文浩自己記得更清楚,還會打電話來提醒。
有了家人的這層牽絆,文浩情緒穩定了不少。如今,每日服藥已經成了文浩的“肌肉記憶”。他加入了不少病友羣,在感受到共鳴、看到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討論時,文浩也會發言。
他知道,世上有這麼多和自己一樣的人,大家同病相憐,但仍在探索治療方案,努力生活。羣友們互相分享日常生活,彼此打氣,緩解了文浩的大部分焦灼情緒。
病友們報團取暖,讓文浩覺得,日子又有了盼頭。碰到其他剛確診,處於低谷期的感染者,文浩也會用當初醫生的話勸慰說:“先把藥喫上,一切都還來得及。”他不再是17歲初確診時的絕望少年,滿滿的篤定感,就像一艘進港靠岸的船。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內容來源:海岸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