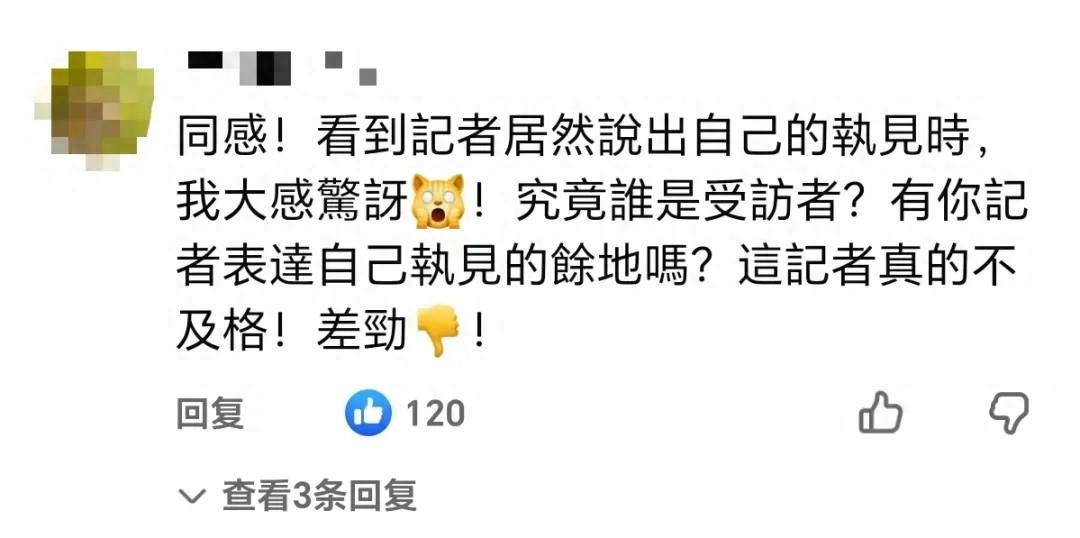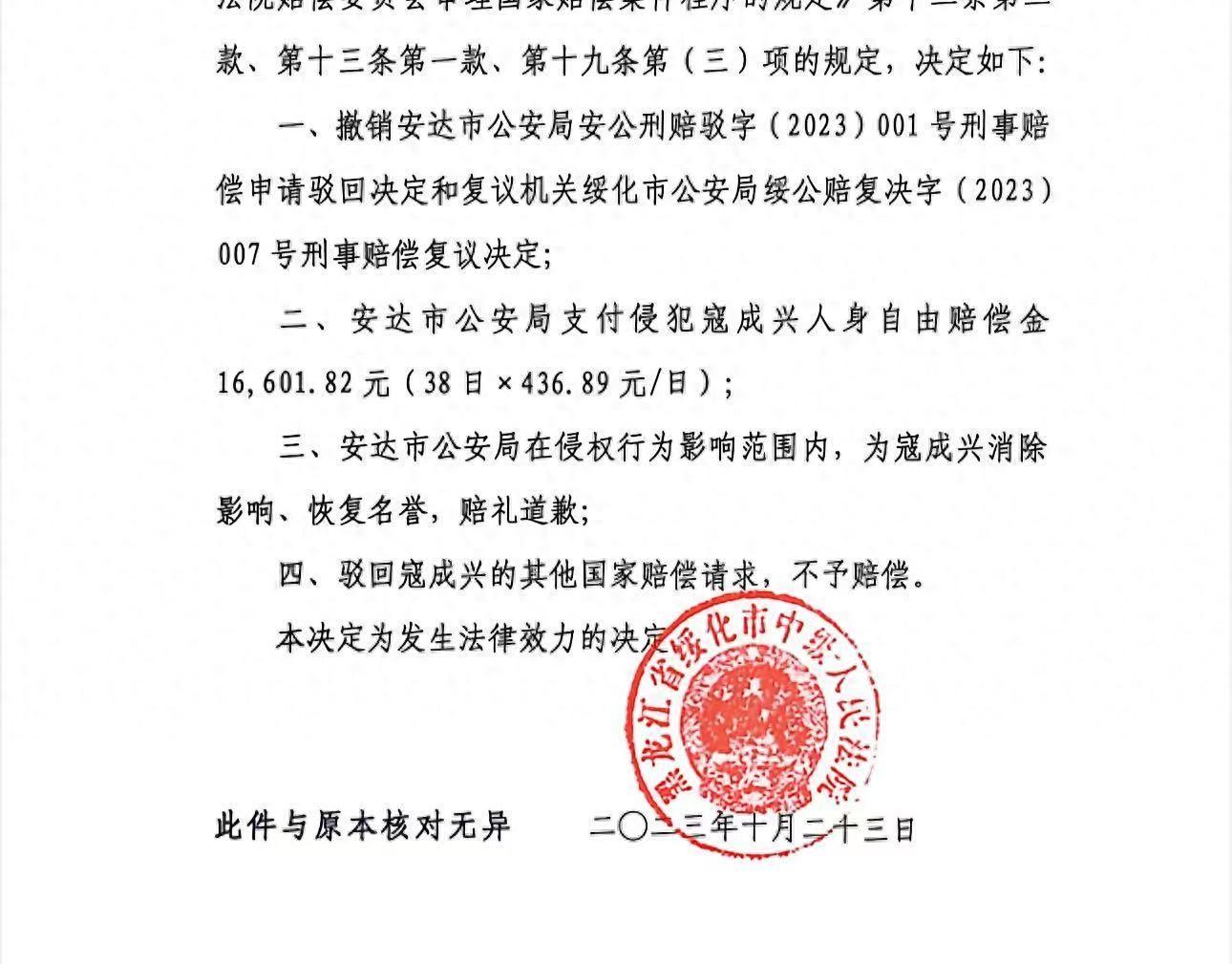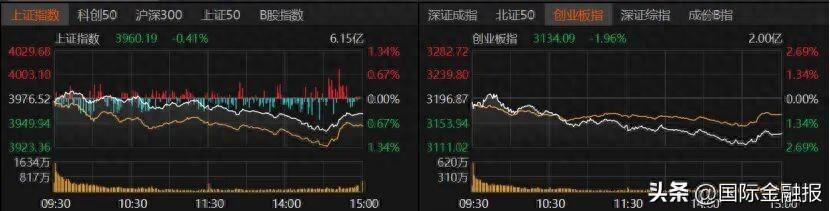11月4日,中方會見訪華的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評價中俄關系“在風高浪急的外部環境中篤定前行”。
據俄羅斯塔斯社報道,米舒斯京11月3日先到杭州出席中俄總理第三十次定期會晤,會談重點將放在發展經貿合作、物流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加強能源夥伴關係以及拓展高科技和農業領域的合作,次日又到的北京。

長期關注俄羅斯新聞的朋友或許會有一種感受,普京幾乎是“不理內政”的,把所有國內事務都交給了專業官員團隊,以至於俄國國內事務的存在感極低。
稍微看點新聞的中國人都認識紹伊古、拉夫羅夫、格拉西莫夫等人,但能叫出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名字的卻不多。
拋開普京自己做俄羅斯總理的那四年不談(2008~2012),在他做總統的19年裏,俄國其實已經換了好幾屆政府:
米舒斯京: 2020至今
梅德韋傑夫:2012~2020
祖布科夫: 2007~2008
弗拉德科夫:2004~2007
卡西亞諾夫:2000~2004
至於說普京本人,他的精力主要集中於國際事務,身邊經常是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外交部長等官員,現身背景要麼是戰鬥機、核潛艇,要麼就是各種國際關係性質的論壇。
與其他俄羅斯高級官員不同,米舒斯京長期專注內政,是俄烏戰爭期間極少數沒有激烈批評西方的莫斯科高層,也被認爲是非普京核心圈子成員。
按照俄國法律,總統換屆後總理必須率領內閣總辭,新總統重新提名總理人選,在總統辭職或不能履職時,總理作爲第一順位繼任人擔任臨時總統。

普京發表國情諮文時,臺下就坐的俄羅斯軍政大佬,C位爲米舒斯京。
接下來切入正題。
如何看待俄羅斯對我們的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也極具爭議的問題,概括來說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觀點A:俄國明顯進入了國運下行通道,美國試圖將中俄做綁定。
美國地緣政治大師斯皮克曼有一句名言:“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很可能造成一個國家命運的終結,而且這種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轉的。”
這句話適用不適用於美國暫時很難講,但至少很適用於俄國。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蘇聯/俄羅斯其實始終處於持續衰落的歷史進程中——蘇聯解體是其中一個標誌性事件,此次俄烏衝突或許會成爲另一個標誌性事件。
正如蘇聯的分崩離析一樣,這種衰落是內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含人口減少、民族矛盾、經濟滑坡、西方制裁、戰爭泥潭等等,並反映在軍事、科技、政治、社會、國民經濟等各個領域。
普京總統希望將俄國拉出歷史的下行通道,重振帝國雄風,但即使在投入資源最多的軍事領域,效果也是不明顯的。
即使未來某天俄烏實現停火,可以預見俄羅斯也很難恢復元氣。
A觀點認爲,美國試圖把中俄綁定在一起,誘導中俄建立同盟關係,然後利用俄羅斯在國運下行通道期間的“掙扎行爲”爲中國廣泛樹敵,藉此團結整個西方世界來對抗中國。
因此中國有必要與俄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提前制定好可能需要做切割的場景預案,對俄支持的底線決不能超過美國和西方對華實施聯合制裁的底線。
持A觀點的朋友還有一種遠期設想——遭到嚴重弱化的俄羅斯不代表對中國就一定不利。
一個弱化的俄國符合中美歐三方利益,甚至還可能引起美國與歐盟的矛盾,因爲缺乏俄國的威脅後歐盟就不再需要緊密的跨大西洋關係,有助於法國等大國實現“戰略自主”。

觀點B:現階段中國無法找到合適替代俄羅斯的戰略伙伴,美國的思路是先歐後亞、先弱後強、各個擊破。
B觀點認爲,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衝突升級有助於轉移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地緣壓力,中國哪怕不對俄施加軍事援助,至少應該力保俄羅斯不垮臺。
普京之所以在戰爭狀態下仍然受到俄國民衆高度支持,除外部壓力產生的凝聚效應外,很重要的一點便是俄國經濟能夠正常運轉——中國產品基本了滿足俄國民衆的日常所需,讓西方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持B觀點的朋友還對A觀點抱有一種疑慮:中國即使卸下俄羅斯的包袱,也不太可能實現與西方的和解。
比如經貿領域的脫鉤與去風險,其實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俄烏衝突只能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
反過來,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國當下“和平解決烏克蘭紛爭”的外交敘事屬於折衷方案,假如戰事一邊倒向俄羅斯,可能又是另一種敘事,即中方的任何政策轉變都會被解讀爲“被迫轉向”。
總之,B觀點認爲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了,所謂的“一個弱化的俄羅斯更容易引起歐美矛盾”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象。
回顧歷史,工業、科技領域的產業鏈升級與高端軍事裝備、地緣政治格局、全球權力分配等要素密切相關,每一個走到發展節點的新興大國都將面臨守成霸權的打壓與阻擋。

俄烏戰爭讓美國重新獲得在西方世界的絕對領導地位,把試圖脫離軌道的法國和德國重新帶回北約框架。
觀點C:兩難選擇之下,只能採取相對保守的做法,等待有利時機。
持C觀點的朋友認爲,現階段與俄羅斯劃清界限是一種風險很大的舉動,而且在承擔風險的同時看不到“確定的收益”。
正因如此,中國只能夠暫時維持在B的框架下前進,併爲此承受與西方關係一步步惡化帶來的代價。
那什麼時候中方可以獲得相對靈活的選擇呢?歐盟、俄羅斯任意一方迫切希望停戰的時候。
目前歐洲、烏克蘭與俄羅斯尚未達到精疲力盡的時候,各方對於戰局前景的認知存在極大偏差,且普京總統性格上不太容易做出明顯讓步,因此勸和促談根本無從下手,中國只能被動等待時機。
說一千道一萬,無論A觀點還是B觀點,他們都在極力避免一種場景——戰後的俄羅斯元氣大傷,導致西方與反西方力量失衡,更多中間地帶國家倒向西方,中國變得更加孤立。
因此持C觀點的朋友認爲,在俄烏僵持期間,中國最需要做的事情是發展自己和儘快整合全球南方力量。
即讓俄國儘可能長的拖住西方,爲中國爭取經濟發展與整合發展中國家的時間,獲得另一種形式的“戰略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