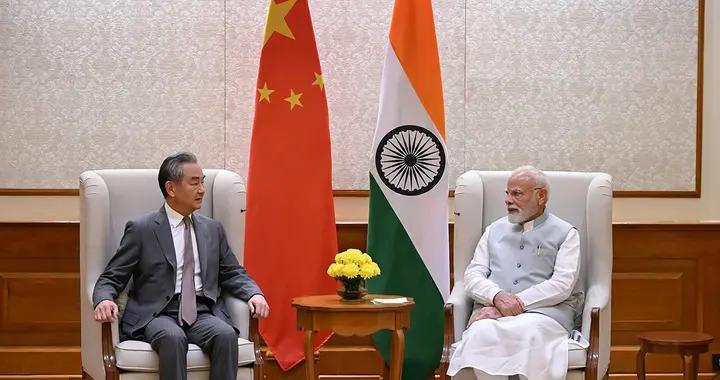滴滴清泉北上流,千里水脈潤北方,這項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超級工程,正悄然改變着中國的命運。
打開水龍頭,清澈的自來水嘩嘩流淌,北京居民王冬梅端起一杯水細細品嚐:“水很甘甜,直接喝沒問題。”她回憶說以前水質很差,水鹼很多,家家戶戶都得安裝淨水器。

這水竟來自千里之外的湖北丹江口水庫——這是一條不在自然地圖上標註的“地下長江”。
北方缺水的問題困擾了中國幾千年。廣袤的華北平原上,城市日漸繁華,田疇連綿不絕,但地下水位卻連年下降。河北的農民爲灌溉爭搶水源,井越打越深,水卻越來越少。
南北水資源的差異驚人:長江一年的水量將近黃河的20倍,中國境內流量超過黃河的15條河流中,12條在南方。面對這種困境,一個大膽的構想自上世紀誕生——讓南方的水北上。
1952年,毛澤東視察黃河時,首次提出了“南水北調”的構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 這個宏偉構想在當時看來幾乎不可能實現。
橫跨中國地形的三大階梯調水,工程難度超乎想象。中國地形西高東低,大江大河大多自西向東流,而南水北調卻要讓水逆自然規律北上。

經過幾十年論證,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開工。規劃了東、中、西三條線路,連接長江、黃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水系,構成中國北方地區“四橫三縱”的水脈格局。
工程規劃最終調水規模448億立方米,建設時間需40-50年。建成後將解決700多萬人長期飲用高氟水和苦鹹水的問題。
東線工程面臨一個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礙——揚州地勢比山東低40米,水需要從低處往高處流。
工程師們創造了奇蹟:建造13個梯級泵站、160臺大型水泵,將長江水一級一級往上提。這就像是用水桶從井裏打水,泵站充當了“大力士”,幫助水流爬過陡峭的“階梯”。
東線工程利用京杭大運河這條古老大運河的脈絡北上。但新的挑戰出現——水質問題曾經非常嚴重,上世紀的京杭大運河水質差得“連魚蝦都活不下去”。

面對挑戰,江蘇地區關停了800多家污染嚴重的化工企業。山東也關停了500餘家高污染企業,並建造了許多污水處理廠。經過治理,東線水質從“劣五類”提升到飲用水級別。
中線工程選擇了一條更直接的路線——從丹江口水庫自流引水,全線開鑿一條全新的人工河道。
中線工程最令人驚歎的是“穿黃工程”。讓南方的清水與黃河水相會卻不混合,工程師們在黃河河牀下方37米處挖掘了兩條長4250米的隧洞,讓長江水從黃河身軀中靜靜穿過。
爲確保水質,丹江口水庫周圍的居民進行了搬遷,保證了水質的純淨。如今,中線水質始終穩定在地表水Ⅱ類水平。
2014年,河南省遭遇63年來最嚴重夏旱,平頂山市百萬人口面臨斷水危機。尚未正式通水的中線工程臨危受命,緊急調水支援。當丹江水與澎河“會師”那一刻,現場人羣激動不已,這水真正成了“救命水”。

南水北調工程累計調水量已達800億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85億人。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相當於再造了一條黃河!
對於北京這樣的資源型缺水特大城市,“南水”已佔城區日供水量的七成以上。北京密雲水庫蓄水量自2000年以來首次突破17億立方米,提高了首都水安全的戰略儲備。
天津市南開區的張愛雲老人對水質變化感受深刻:“‘南水’好喝得多!”她回憶過去自來水是苦的、鹹的:“越喝越覺得渴。洗頭是澀的,總覺得洗不乾淨。”如今,苦鹹的自來水已成爲歷史。
河北省城市供水逐步切換爲南水北調水源後,滄州、衡水、邢臺、邯鄲等市徹底告別了祖祖輩輩飲用苦鹹水、高氟水的歷史。
當東線和中線已經發揮巨大效益時,西線工程正在積極推進中。這條“水動脈”規劃從長江上游“借水”注入黃河流域,解開西北乾旱的困局。

西線工程計劃通過超長深埋隧洞穿越巴顏喀拉山,打造一條能自流的引水主軸線。這條“水動脈”並非孤軍奮戰,而是規劃了9條沿河補水線和4條供水專線作爲“毛細血管”,最終形成覆蓋青海、甘肅、寧夏等省區的“一軸三帶十片”水網格局。
2025年以來,西線工程前期工作進入“加速度”模式。四川作爲水源核心區,正深化雅礱江、大渡河的調水方案;甘肅聚焦受水區建設;青海則推進“調水+新能源”的融合模式。
西線工程建成後,預計年調水量可達80億~170億立方米,相當於黃河年徑流量的1/3,能直接惠及超1億人口。
如今,南來之水已成爲北方地區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截至2025年7月,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已累計調水突破800億立方米,曾經乾旱的華北平原,地下水位開始回升,河流重現波光。

中國的治水智慧從大禹開始,延續至今,未來西線工程將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動力,改寫中國水資源分佈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