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0~3歲的寶寶誰來帶?送到什麼樣的托育機構(託兒所、托育園)才能讓父母放心?大力發展0~3歲普惠托育,既是民之關切,也是“國之大者”。
在國家發改委支持下,小茱園長帶領團隊在高質量普惠托育方面闖出了一條新路。我們邀請她講述每天發生在托育園裏的故事,讓托育服務被更多家庭接納和認可,共同營造一個生育友好型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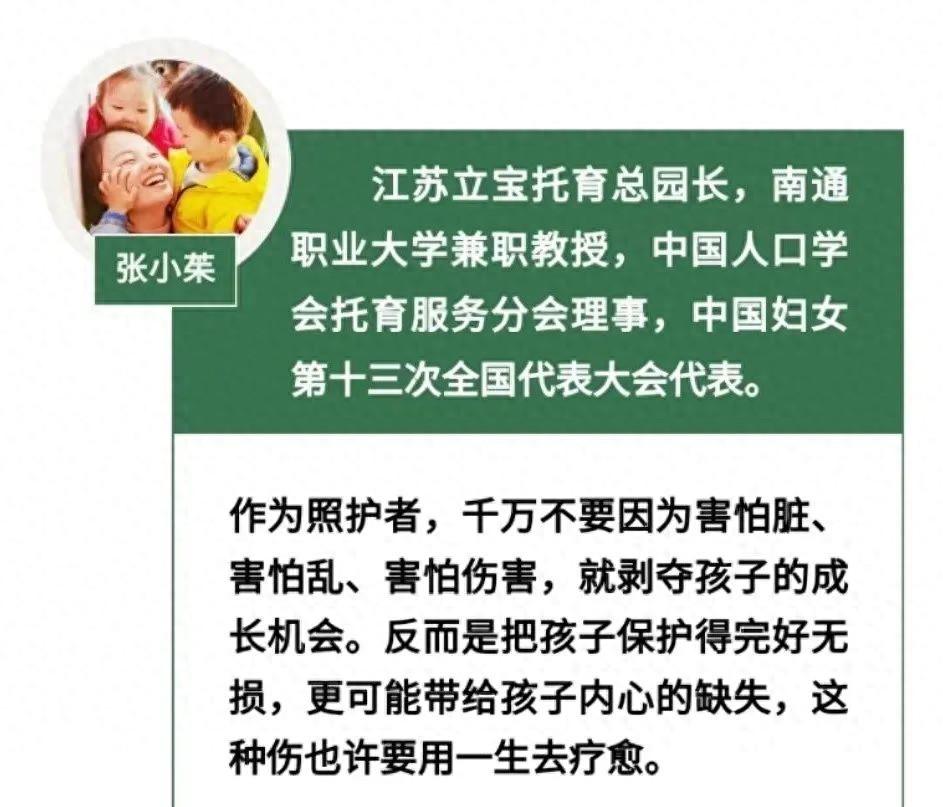
一大早,慧慧老師就拿着一本塗色本找到了我:“小茱園長,可欣的奶奶今天又把這個塗色本帶到了園裏。她要求我們必須讓可欣保質保量地畫滿3頁。”
我記起來,上週五,可欣奶奶就把這個塗色本帶到園裏,要求保育老師安排可欣抽空兒畫。由於立寶園倡導0~3歲嬰幼兒的藝術啓蒙應專注於感官探索,禁止規定性藝術指導,所以,園裏一直堅持不接受家長此類的“加課”要求。發生這樣的事情,需要主動和家長溝通解釋一下。
“可欣的爸媽有什麼想法嗎?”我問道。“週六,我給可欣媽媽打過電話了。”慧慧老師的工作還是很用心的。“我得知,這個塗色本是可欣奶奶買回家的,可欣爸爸堅決不同意讓孩子塗色,雙方還因此鬧了點兒矛盾,於是,老人便偷偷把塗色本帶到園裏來了。”
我問:“你知道可欣爸爸爲什麼堅持不讓孩子塗色嗎?”慧慧老師反應迅速:“可欣爸爸覺得,隨着人工智能時代到來,規則明確的重複性工作越來越不重要了。過早接觸這些塗色畫畫,不僅意義不大,還可能固化孩子的思維。”
我又問:“那可欣奶奶爲什麼這麼堅持呢?”慧慧老師說:“奶奶朋友家的孫女和可欣差不多大,人家孩子不僅塗完了整整一大本,還因此認識了水果、動物、日用品等。她覺得我們園不教孩子學知識,不太好。小茱園長,您的辦法多,能不能幫着勸勸可欣奶奶啊?”我不由得嘆了口氣。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分歧,不是簡單講講道理就能解決的,必須另闢蹊徑。
週六,我們準備了一場以遊戲爲主的家長沙龍活動,特別邀請了可欣奶奶、爸媽以及其他有類似分歧的幾位家長參加。
沙龍分爲“百變星君”和“情景再現”兩個模塊。在“百變星君”環節,我們下載了AI唱歌、AI剪輯、AI創作、AI畫畫等4款AI應用軟件,供大家根據抽籤選中的職業來配套使用。
可欣奶奶抽到的是“歌唱家”,她有點兒爲難:“我五音不全,玩兒不了啊!”“有AI唱歌幫你,很簡單的!”可欣爸爸耐心地教母親打開軟件對話框,根據AI的寫歌要求,輸入關鍵詞和意境。
奶奶想了一會兒,輸入“兒歌、歡樂、2歲孫女和奶奶在玩耍、祖孫情誼等相關信息”。點擊“創作”後,屏幕立刻跳出一首名爲“糖融祖孫情”的歌曲創作進度條,以及“預計等待5分鐘”的提示。“這個名字好奇怪啊!”“這是AI創作的名字,如果您覺得不好的話,可以自己修改。”正聊着,軟件顯示作品已經完成了。
“這麼快!”可欣奶奶很驚奇。“祖孫之情甜蜜如糖溶化,圍裙系滿了愛和牽掛。”開頭一句歌詞就很打動奶奶,她追問:“那現在怎麼唱呢?”可欣爸爸點開“新建音色”按鍵,讓奶奶根據提示邊讀邊唱一些文字來截取音色,並加載進去,點擊“播放”鍵,可欣奶奶的“獻唱”就開始了。
“這真是我的聲音啊!”可欣奶奶一臉震撼與驚喜。“可欣奶奶,您覺得在創作過程中,最關鍵的是什麼呢?”“應該是我輸入的那些關鍵詞。”我點點頭,邀請其他家長參與,他們在驚歎中體驗了AI繪畫、剪輯和寫作。接下來,我又安排了“情景再現”環節。請每家各選一位家長,帶着孩子完成塗色本里的蘋果、香蕉和帽子3幅圖案的塗色,要求是儘量畫得和示範圖一模一樣。

人工智能時代的育兒智慧
我們用視頻錄製下了整個過程,然後現場回放。有的寶寶在塗鴉中,把油畫棒放在嘴裏,負責引導的家長立馬制止:“這個不能喫!”然後便一直關注孩子會不會再次將畫筆放在嘴裏,並不斷去提醒。
仍處於用感官探索世界階段的2歲孩子,並不理解家長擔心油畫棒成分是否有害,誤以爲塗色是錯誤的行爲,臉上露出了不確定和自我懷疑的表情。
有的寶寶在塗蘋果的時候,選擇了紫色的油畫棒,家長立馬糾正:“蘋果應該是紅色的。”雖然孩子並不情願,但在家長一而再、再而三的引導下,最終換成了紅色。還有的寶寶不小心塗出格子,家長便會手把手教他。
視頻結束的時候,整個教室出奇安靜。我試着對這次沙龍活動做引導性的總結。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曾提出“預設性干預”的概念和心理警示,成年人基於自身經驗或社會規範,在孩子探索前預先設定行爲規則、結果標準或操作路徑,實質是用成年人的思維框架替代孩子的自主認知建構。
這樣的預設指令不僅會抑制創造性思維的發展,還會弱化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當孩子發現現實結果無法達到預設標準時,可能產生持續的挫敗感和自我效能剝奪感,逐漸形成“我需要被指導才能行動”的依賴心理。有研究表明,自由塗鴉時幼兒前額葉皮層的激活度是填色練習的3.2倍。
塗色活動可作爲偶爾的趣味遊戲,但如果成爲主要活動,可能付出“短期技能進步、長期創造力萎縮”的代價。保護孩子與生俱來的“亂塗亂畫的勇氣”,遠比“畫得像”更重要。過早要求嬰幼兒遵循固定框架塗色,本質是培養“標準化思維”,而未來社會需要的恰恰是跳出框架提出新問題、創造新價值的“非標準化人才”。
未來很多工作會被AI取代,有預測表明,到2040年,72%的規則性工作將被AI取代。但是人類的創造力、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情感理解是AI難以替代的,所以,我們要永遠保有提出新問題、定義新價值、創造新可能的原始衝動。這正是我們要傳遞給下一代的生命火種,讓孩子們有能力打破AI侷限,成爲設計新畫框的人。
這是一場已經悄悄開展的育兒革命,它正在重新定義人與技術的共生關係。當AI能完美復刻《蒙娜麗莎》時,我們更需要孩子敢於畫出3隻眼睛的微笑;當算法能瞬間填滿所有色塊時,那些溢出邊界的線條,纔是人類文明最珍貴的遺產。正如可欣在節日賀卡上塗抹的橫跨整張紙面的紫色—那不是錯誤,而是孩子對未來的大膽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