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的夏天,精神病學和人類學家Arthur Kleinman教授訪問中國,他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在過去,和美國相比,中國的抑鬱症患病率非常低,但大量精神科和內科的病人被確診爲「神經虛弱」。
這一現象在後來的很多研究中得到證實,許多中國患者前往精神科求助時,都以軀體症狀而不是心理不適爲主訴,中國人的軀體化報告率遠高於西方人羣, 在抑鬱症患者的臨牀報告中尤爲明顯(Nikelly,Arthur. 1988)。
在我們所處的東亞文化中,大多數人往往不善表達情緒,加之社會對心理問題的接受度較低,人們更傾向於用「身體疼痛」來描述內心的焦慮和困擾(Kirmayer & Young,1998)。
來到21世紀的今天,情況並沒有好太多。正如今天故事裏的4位主人公,當他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遭遇情緒危機時,最先「表達」的依舊是身體:月經失調、胃痛、溼疹、失明……
他們求醫問藥,卻得不到任何診斷結果。兜兜轉轉最終才意識到,原來是身體不得已在用疼痛提醒我們,該關照自己的情緒了。
以下是這4位朋友的講述:
2023年,我大四,正在一段曖昧了好幾年的關係中苦苦掙扎。我們相識於社交軟件,對方一直對我若即若離,我的情緒也隨之波動很大。
6月份,我實在受不了這種狀態,就和對方互刪了。在我看來,這只是賭氣,沒想到8月份就收到了對方結婚的消息。
我迎來人生第一次分手,加上還面臨畢業和考研的壓力,整個人的情緒陷入谷底。
兩個月後,我的月經沒有按時來。我以爲那個月推遲了,沒想到,這一推遲就是10個月。
伴隨閉經,身體還爆發了很多問題:長胖30斤,從來不長痘的皮膚開始冒痘,火氣也越來越大……我當時很害怕,身體出了什麼大問題?是不是長了個瘤子?
我把這種焦慮轉化成去醫院的行動,3個月去了30趟醫院,平均每3天就去一次。我去了上海皮膚科最好的兩家醫院,從掛號費幾十塊的到五六百的主任、副主任醫生都看了,還做了兩次全套內分泌檢查,看了中醫。
沒有任何明確的診斷結果。
當我問這些症狀是什麼原因呢,中西醫都說只是內分泌失調,雌激素低,讓我回家食補,喫點燕窩。還有一個內分泌科醫生說我是身材焦慮,讓我不要減肥了。

那個時候雖然同時在看精神科和其他科的醫生,但治的是不同的問題——心理和身體,我沒想過把二者結合起來,也沒人告訴我這一點。
傷痛只能靠時間療愈,後來我試着接觸其他男生,雖然沒有遇到特別喜歡的,但情緒狀態慢慢好一些了。
10個月後,月經忽然來了。我也不知道具體什麼原因,其他症狀也有好轉,於是我就着手準備考研了。
但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大概4、5個月後,月經又開始淋漓不盡,量不大,但能持續很久,有半個月、二十多天。這個時候,我遇見了第三個中醫,她提醒我月經時間過長,以及之前的閉經,很可能是情緒問題導致的。
我仔細回想了一下,的確是這樣,每次月經不調跟我的情緒變化都是一致的。於是,我把之前的經歷串聯起來,失戀的打擊、考研的學業壓力,每次出現一個新的壓力事件,情緒崩不住了,月經都會出問題。
意識到這一點後,我整個人放鬆了很多,本來還打算去做B超、喝中藥什麼的,這次之後我就決定徹底不看(醫生)了。很奇妙,心態放鬆之後,月經又逐漸恢復正常了,怎麼也看不好的病,莫名其妙就好了。
我感覺女孩子對月經這類婦科問題還是比較羞恥的,但很多婦科問題其實都和情緒有關。我有一個朋友月經也不是很正常,量很大,一來就特別多,但她很討厭看醫生。還有個朋友是多囊卵巢綜合症,喫了一段中藥總想吐就不喫了,大家都沒有進一步關注這個問題是爲什麼,沒往情緒方面想。
現在我把月經當作瞭解情緒的信號,我會記錄月經週期,肯定不會閉經超過兩個月還置之不理,如果有異常就去找自己的情緒哪裏出了問題,不像之前只會陷入對身體的恐慌。
女性的身體是很靈敏的,而很多時候人對自己情緒的覺察和感受,總會遲鈍一點。

《美食祈禱戀愛》
我沒有胃病,平時也很少覺得哪裏不舒服,但是去年三四月,寫論文初稿的時候,我開始出現規律性胃疼。每天上午10點、11點,下午3點、4點,一陣一陣絞痛,明明沒有到喫飯的時候,總感覺胃裏空落落的。
現在想來,胃痛最頻繁的那個階段,正好在寫整篇論文裏我最難熬的部分,每寫一句話,都要先翻閱大量資料,看看別人是怎麼設計、分析、解釋的,然後換成自己的語言,再整合到自己的邏輯裏。
我是一個很容易在內容質量上糾結的人,但也常常因此給自己造成更大的負擔。一邊想着「快點寫完結束痛苦」,一邊又忍不住覺得「寫成這樣太水了吧」。很像小時候考試,明明就要交卷了,但還是不會做,於是焦急、難受、緊張,讓人抓狂。
但論文的痛苦似乎更勝一籌。上學的時候好歹有標準答案在等你,可論文沒有答案,你得自己創造問題,再創造一個合理的回答。誰也不知道你的回答對不對,甚至連你自己都不知道,這種沒有參照系、沒有邊界的創作,對我來說太不安了。
在這樣的焦慮中,胃開始疼了。我有些擔心,跟同學說想去醫院看看。或許焦慮環境中,大家都有相似的體驗,他告訴我不用擔心,「你可能是寫論文寫應激了」。
那時候恰逢五一,我回家後和家人相處,徹底放鬆休息,完全沒有再碰論文,神奇的是,胃真的沒有再疼,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麪包和湯和貓咪和好天氣》
我這才意識到,情緒原來會以「胃疼」這種方式表達出來。雖然這段經歷沒有嚴重影響我寫論文的節奏,但它確實讓我發覺,我一直習慣於靠意志力硬撐,但身體比我誠實,它不會說謊,也不會陪我演。
在確定不是嚴重的健康問題之後,我就不那麼在意了。但我是個比較敏感的人,會羨慕那些面對壓力也能很鬆弛的同學,於是我開始學習心理學相關內容,想讓自己變好一點。
但情緒這件事,對我來說始終很難完全掌控。它不像一個題目有對應的答案,有時候你覺得自己還好,可身體卻會告訴你,你其實很緊繃。
爲了讓自己更早能覺察到壓力,我前段時間給自己買了個智能手錶,裝了一個應用,能實時監測我的壓力狀態,從「狀態優秀」到「壓力過載」,顏色標識很清晰。
我發現它的判斷真的挺準的,我能更及時意識到自己的壓力情況。我現在還會用手錶裏的正念 app,每天做一到兩次一分鐘的深呼吸練習,這種簡單的動作,也很有用。


有時候我也在想,軀體化並不全是壞事。就像在播客節目「張春酷酷酷」裏說到,我們的大腦很笨,它只會讓我們一直一直工作。但身體很聰明,面對壓力的時候它會首先發出信號。告訴自己現在太累了,需要休息了。
我想,以後再遇到類似的任務時,我可能還會緊張焦慮,但我不會再那麼如臨大敵,也不會覺得只是「沒喫早飯」這麼簡單。我會停下來,聽聽它到底想告訴我什麼。
我膝蓋的疼痛斷斷續續持續了快 3 個月。在心內科,骨科,皮膚科,全部查過都沒有問題,西醫說可能是髕骨軟骨炎,開了口服藥,也貼了膏藥,沒好。看過中醫,敷過草藥,做過鍼灸,還是不奏效。
在學校上樓梯都只能扶着扶手一點點上,下樓梯更疼,只能側身一階一階慢慢走。有時手指指尖也強烈脹痛,按壓也按不下去,能夠感覺到手指指尖有動脈搏動的感覺,和心臟一起跳動。
父母忙於分家,也沒有時間關注我。身體始終沒痊癒,情緒也越來越差,我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平時喜歡的興趣班也頻繁翹課,就在家待著。
最終父母帶我去了精神科,看了醫生,確診了抑鬱症,但因爲喫藥斷斷續續,好像情緒和身體疼痛也沒很大改善。
印象最深的一次,母親因爲副作用和藥物費用問題,不想讓我再喫藥。當時爆發了嚴重的爭吵,我回到自己房間裏,把門嘭地一下關上,她一直不停地敲門、砸門。我當時非常害怕,加上情緒激動,頭嗡嗡發暈,甚至想從窗戶跳下去。後來身體開始難受,膝蓋和手肘又疼痛起來。
真正意識到這些疼痛是情緒問題,是到了大四。當時因爲疫情和工作,壓力很大,我找了心理諮詢師。初步溝通過後,他問我現在身體有什麼感受。我剛開始諮詢,自己也說不清楚有什麼感受。但是他說,聽完我講,他覺得肩膀很痛,問我會不會有類似的感覺。
自己揹負了太多東西,所以肩膀會抗議;強行拖着自己走得太快,所以膝蓋也會抗議。

現在不在家,不用和父母打交道了,也可能是找了諮詢師,有了情緒宣泄的出口,疼痛的範圍小了些,不那麼頻繁了,但也沒有徹底消失。
後來偶爾會因爲和父母吵架,半夜驚醒,又開始劇烈地疼痛。工作環境壓力太大時,疼痛也會捲土重來,有時痛到用手砸牆,只能深夜發消息給諮詢助理問能不能加一次諮詢。諮詢師會提醒我說,其實可以在更早一點的時候告訴他。
從那之後,我開始練習察覺疼痛的信號。我回憶起來,每次疼痛發作時會先有一陣頭暈,於是我試着「往前一點」地發現它。這樣「往前一點」的練習,我做了一年,才逐漸掌握。
現在,如果覺察到頭疼的跡象,我會閉眼深呼吸一會,有空就做一下冥想。如果沒能緩解,會緊急聯繫我的諮詢師。諮詢之後還是沒辦法緩解的話,我會申請調休一天,讓身體和情緒一起慢下來。
與疼痛共存的第8年,我已經逐漸接受了。它就這樣,消失一段時間,又繼續出現。如果我全力去對抗和消滅它,只會精疲力盡。所以,我會想象自己站在一旁,看着疼痛發生,再看着它離開,就像月經一樣,到來,然後消失。
我是一個鋼琴老師,很早就出國了。2016年左右,有一天我正在練琴,突然就看不見了,眼前一黑,好像閉上了眼睛一樣,時間沒持續太久,大概幾秒鐘。
一開始我還以爲是不是太累了,但後來這種情況(失明)發生的頻率很高,有時候是眼前出現一坨黑色的東西。我才覺得不太對勁了,準確地說,我意識到「它」又來了。
眼睛失明不是一次出現了,最早小時候練琴的時候就出現過。但以前沒這麼頻繁,是偶發性的,就沒太當回事。
但這次,我決定直面它。
我心裏已經隱隱感覺到可能和心理問題有關,因爲我對自己的身體很瞭解,應該沒什麼器質性的問題,但我一直是個特別壓抑自己感受的人。
小時候父母工作忙,把我送到幼兒園的「長託」,要在幼兒園喫飯和睡覺,相當於住在了那裏。我特別恐懼,一直哭呀哭,有一天就嘆了口氣,心死了,只能接受。
也可能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試着屏蔽自己的所有感受,因爲覺得沒有用,不需要有它(感受)了。
很快家裏人讓我學鋼琴,從小學開始,每天雷打不動練至少兩個小時,我經常跟我媽發生爭執,想出去玩,但一次都沒有成功過。我其實一直不喜歡彈琴,但這麼多年還是彈下來了,幾乎已經成爲了我的一部分。
接着到了初中,家裏發生了一些變故,媽媽去了國外工作,我在國內跟着爸爸搬家,轉學,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現在想想我當時應該很崩潰吧,但因爲早早屏蔽掉了自己的感受,並沒有太多情緒。
不過那個時候,身體開始提醒我了,我的右邊肩胛骨處出現一片非常頑固的溼疹,從此「陪伴」了我二十幾年,再也沒有徹底消散過。
對,失明不是我的第一個軀體化症狀,在那之前是溼疹。回到出國後的失明,可能當時壓力太大了,第一道防線(溼疹)已經被擊潰了,身體不得不給了我更嚴重的信號。
我當時去的是歐洲的維也納,一個講德語的國家,在國內英文學得再好也沒用了。加上當時做音樂人掙錢很難,我就規劃轉行,做一些和藝術策展相關的東西。
所以那幾年是非常高壓的的狀態,語言的壓力,意識形態的壓力,生存的壓力,所有東西都擠在了一起,一直沒有喘息的機會。我對自己的要求又很高,覺得回國就是混不下去了,沒出息,就這麼硬撐着。
我現在回想,眼睛看不見可能也是當時潛意識裏渴望的,眼不見,心不煩,能逃避眼前的困難。我不允許自己逃避,身體來幫助我。

Molly最喜歡的席勒的畫
「畫中的線條好像曾經出現在我眼海中的黑線」
意識到失明可能是心理問題後,我就去找了心理醫生。那是我關注了很多年的一個心理醫生,就是爲了以備不時之需,我很多年裏都是一種內心不安的狀態,總覺得會在什麼時候需要她的幫助。
就像水管堵了要找一個通水管的人,心理醫生幫我捋順了一些東西。當時我就覺得一切都說得通了,安心了,之前雖然有一些隱隱的感覺,但沒有另外一個人來確認這些感受。我還記得跟心理醫生講述我的經歷時,她很快就說,你已經很棒了。我這才意識到,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承擔了太多東西,而且一直在勉強自己。
看了心理醫生沒多久,失明的症狀就好了,我也是這個時候才知道,哦,這是「心因性失明」(注:心因性失明是一種精神心理因素導致的視力障礙,並非眼睛本身存在器質性病變,強烈的負面事件都可能成爲心因性失明的誘發因素)。所以如果能接受醫生給你傳遞的信息,好好消化她的話,軀體化的症狀自然就會有好轉,主要取決於你的接受度。
之後我的眼睛也沒再出現過失明的情況,溼疹還是會冒出來,但沒有之前那麼嚴重了。每次溼疹出現的時候,我就會多關注一下自己的情緒,是不是又在勉強自己?我知道一定得好好調整,不然眼睛還是會出問題。
我的舅媽是一個護士,她跟我說過,出溼疹是因爲你的內心不平靜,需要靜養。好像真的是這樣,每次我度假、休息的時候,溼疹就會好很多。我現在也不用任何藥,逮着機會就讓自己舒服,不一定真的能很平靜,但儘可能地讓自己愜意,開心。
我也很感謝自己的身體,這些年,我過得這麼辛苦,它依然還在拼命保護我,我們互相照料,互相合作。所以有時候哪怕我努力讓自己放鬆了,身體的症狀還是沒有緩解,我也知道它盡力了,就借這個事,讓自己多開心開心。

《黎明的一切》
相關推薦
相關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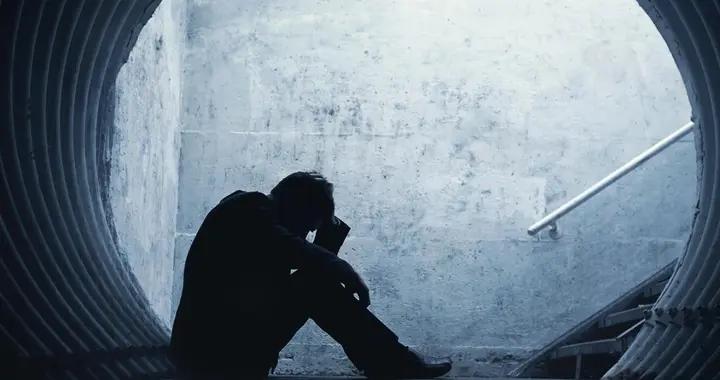
抑鬱症加強迫症是怎樣的痛苦?藥喫了十年,最後我還是果斷放棄了
-

趣味心理學丨斯特魯普效應與心理健康
-

如果你抑鬱很厲害,喫藥不見改善,建議你死磕這1件事
-

【別讓內耗拖垮你的人生|翻篇力,是成年人最頂級的自愈能力】
-

爲什麼明明想「向前走」,卻總懶得動?
-

蔣方舟:「內核強大」絕對不屬於人的天性
-

發現一件可怕的事情:普通家庭最大誤區就是,老人沒義務幫忙帶娃
-

人到中年,請遠離那些收入差距太大的兄弟姐妹
-

歐美智庫預測:2100年中國人口將降至8億,有三大隱患悄然而至
-

你永遠比鏡子中的自己至少醜30%|心理學家解釋你不上鏡的原因
-

如何判斷領導是在培養你,還是壓榨你?心理學家:注意五個細節
-

心理學家阿德勒:你會患上抑鬱症,早在童年就有預兆了





